
沙凉书阁 > > 夜来香(苏晚冰冷)完整版免费阅读_(夜来香)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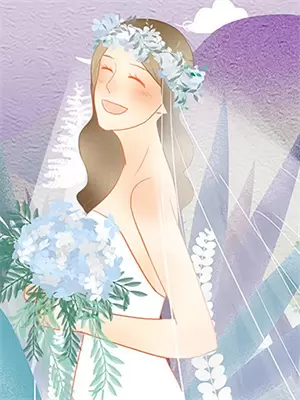
言情小说连载
长篇悬疑灵异《夜来香》,男女主角苏晚冰冷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非常值得一读,作者“时光浅不浅”所著,主要讲述的是:主角为冰冷,苏晚,老孙的悬疑灵异,推理,年代,系统小说《收音机里放着《夜来香》》,由作家“时光浅不浅”倾心创作,情节充满惊喜与悬念。本站无广告,欢迎阅读!本书共计12953字,1章节,更新日期为2025-07-19 14:24:47。目前在本网 sjyso.com上完结。小说详情介绍:收音机里放着《夜来香》
主角:小红,赵慕然 更新:2025-07-19 14:37:21
扫描二维码手机上阅读
雨下得邪性。不是淅淅沥沥那种,是整盆整盆往下倒,砸在筒子楼黑黢黢的水泥屋顶上,
发出沉闷又巨大的轰响,像有无数只巨手在头顶擂鼓。雨水顺着锈烂的排水管哗啦啦淌下来,
在楼下汇成一片混浊的水洼,倒映着家属院那几盏半死不活的路灯,光晕昏黄破碎,
被雨点砸得摇摇晃晃。我撑着把破伞,深一脚浅一脚踩过水坑,怀里抱着个铝饭盒,
里面装着给老娘打回来的酸菜粉条。雨水顺着伞骨缝隙渗进来,冰凉地钻进后脖颈,
激得人一哆嗦。筒子楼像个巨大的、沉默的怪物,蹲伏在无边无际的雨幕里,窗户黑洞洞的,
只有零星几点昏黄的光透出来,聊胜于无。走到三单元门口,收了伞,甩了甩上面的水。
楼道里那股熟悉的、混合着霉味、油烟味和劣质煤球味的潮气扑面而来,
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铁锈气。声控灯坏了很久了,没人修,
只能借着单元门外那点微弱的光,摸索着踩上湿漉漉的水泥台阶。黑暗粘稠得如同墨汁。
脚步声在狭窄的楼梯间空洞地回响,嗒…嗒…嗒…,每一下都敲在自己的心坎上。
走到二楼半,拐过那个堆满杂物的转角,习惯性地往上瞟了一眼——三楼。
整个人瞬间像被钉在了原地,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三楼,301室。那扇门。
那扇紧闭的、落满灰尘、门把手都生了厚厚一层暗红铁锈、早被所有人遗忘的门缝底下,
此刻,竟赫然透出一线昏黄的光!不是幻觉。光线虽然微弱,却异常清晰,
固执地从门底那道狭窄的缝隙里挤出来,在黑暗的楼道地面上,
投下一道歪歪扭扭、边缘模糊的黄色光带。
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的声音,咚咚咚,震得耳膜嗡嗡作响。
一股难以言喻的冰冷顺着脊椎骨往上爬,后颈的汗毛齐刷刷立了起来。301,
这栋筒子楼里无人不知的禁忌之地,那个地方,怎么可能亮灯?半年前,那个叫苏晚的女孩,
就是从这扇门里冲出来,像一只被惊飞的、脆弱的鸟雀,在邻居们惊愕的目光中,
跌跌撞撞冲上楼顶,然后……一跃而下。她摔在楼下那堆还没来得及清理的建筑废料上,
身子以一个极其扭曲的角度叠在那里,身下迅速漫开一大片刺目的暗红。她死的时候,
穿的就是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连衣裙。后来,那房子就彻底空了。没人愿意靠近,
也没人敢住进去。厂里几个不信邪的二流子曾经壮着胆子撬开门进去看过,
回来说里面阴冷得像冰窖,一股子说不出的怪味,灰尘积了老厚。再后来,那扇门就上了锁,
铁锁链都锈死了。可现在,那门缝底下,有光!更诡异的是,就在我僵立当场,
连呼吸都快要停止的时候,一阵极其微弱、断续又沙哑的歌声,
竟然穿透了厚重的门板和外面狂暴的雨声,丝丝缕缕地钻进了我的耳朵里。
“……夜来香……我为你歌唱……”那调子,带着旧时代特有的靡靡腔调,
像是从一台老旧的、接触不良的收音机里发出来的,电流声夹杂其中,嘶嘶啦啦,断断续续。
每一个音符都像生了锈的钝刀片,刮擦着人的耳膜和神经。是《夜来香》。苏晚生前,
最爱哼这首歌。她总是一个人坐在楼下那棵半枯的老槐树下,手里捧本书,
或者就那么望着天,嘴里轻轻地哼着这支调子。她的声音很轻,很柔,像傍晚拂过树叶的风。
筒子楼里的人都知道。
“夜来香……夜来香……”那沙哑、扭曲的歌声还在门缝里顽强地钻出来,
混合着门外震耳欲聋的雨声,钻进我的脑子。空气里那股若有若无的铁锈味,
似乎更浓重了些。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瞬间缠绕住我的四肢百骸,几乎要把骨头都勒断。
我猛地后退一步,脚下踩到一块松动的台阶边缘,发出“咯噔”一声轻响。
怀里的铝饭盒脱手而出,“哐当”一声砸在水泥地上,盖子崩开,酸菜粉条撒了一地,
油腻的汤汁迅速在黑暗的地面蔓延开。几乎是同时,门缝底下那线昏黄的光,倏地熄灭了!
歌声也戛然而止。整个楼道陷入一片死寂,只剩下门外永无止境的、令人窒息的暴雨声。
黑暗瞬间吞噬了一切。刚才那线光,那诡异的歌声,
仿佛都只是我极度疲惫下产生的幻听幻视。我僵在原地,
心脏狂跳得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耳朵里嗡嗡作响,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了头顶,
又瞬间褪去,留下冰冷的麻木。那扇门,那扇301的门,此刻在黑暗中,
像一张沉默的、择人而噬的巨口。我甚至不敢去捡地上的饭盒,喉咙干涩得发紧,手脚冰凉。
定了定神,几乎是手脚并用地逃离了那片令人窒息的黑暗,跌跌撞撞地冲上了四楼,
冲回自己家。“哐当!” 用力撞上自家的铁门,背死死抵在冰凉的门板上,
才感觉双腿发软,几乎支撑不住身体。心脏还在胸腔里疯狂地擂鼓,
每一次跳动都牵扯着太阳穴突突地疼。“怎么了这是?撞见鬼了?”老娘从里屋探出头,
昏黄的灯光下,她脸上满是皱纹,带着几分惊疑。她手里还拿着没纳完的鞋底。
“没……没事。”我喘着粗气,声音干哑得厉害,弯腰把地上的饭盒捡起来,
盖子已经变形了,“摔了一跤,饭……撒了。
”老娘狐疑地看着我惨白的脸和还在微微发抖的手,没再多问,
只是叹了口气:“撒了就撒了吧,锅里还有点剩粥,热热对付一口。脸白得跟纸似的,
赶紧进来,别杵在门口灌风。”我胡乱应了一声,几乎是挪到桌边坐下。脑子里一片混乱,
全是门缝下那线昏黄的光,和那沙哑断续的《夜来香》。那真的是幻觉吗?可那光,那歌声,
还有空气里浓重的铁锈味,都那么真实。第二天一早,雨停了,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
像一块湿透了的脏抹布盖在头顶。筒子楼也活了过来,水龙头边挤满了早起洗漱的人,
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小孩的哭闹声,大人的呵斥声,混杂着各家各户飘出的早饭气味,
一股脑儿涌进楼道。我端着牙缸挤在水池边,冰凉的自来水泼在脸上,
稍微驱散了些许残留的惊悸。但昨晚的经历像一根冰冷的刺,扎在心底。“哎,听说了吗?
”旁边传来压低的声音,是隔壁单元的老孙头,正跟对门的李婶嘀咕,声音不大,
却刚好能飘进我耳朵里。“啥事儿?”李婶正用力刷着一个搪瓷盆。“就昨晚那大雨,
邪乎得很!”老孙头神秘兮兮地左右看看,把声音压得更低,“三单元,
就苏晚跳下去那个301,好像不对劲!”我的心猛地一沉,刷牙的动作顿住了。
李婶手里的动作也停了,脸上露出一丝紧张:“咋?又出事儿了?”“不是出事儿,
”老孙头摇摇头,凑得更近,“昨晚后半夜,雨最大的时候,我们家那口子起夜,
迷迷糊糊好像……好像听见那屋里有动静!”“啥动静?”李婶追问,声音也带上了点抖。
“说不好,”老孙头皱着眉,努力回忆着,“像是……像是收音机?滋啦滋啦的,
还有……还有人哼歌儿?调子怪得很,
像……像苏晚那丫头以前老哼的那个……”李婶倒吸一口冷气,脸都白了:“我的老天爷!
你可别瞎说!那屋锁死了多少年了!厂里不是……”“厂里?”老孙头嗤笑一声,
带着点不屑和愤懑,“厂里顶个屁用!那房子,早有人惦记上了!”“谁?”李婶追问。
老孙头没立刻回答,反而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我赶紧低下头,假装用力漱口,
耳朵却竖得老高。“还能有谁?”老孙头的声音压得几乎只剩气声,带着浓浓的鄙夷,
“就那个……管后勤的张建国!张胖子!仗着跟他姐夫那点关系,在厂里横着走,
早八百年就放出话来,说301那房子位置好,他想要!谁敢跟他争?”张主任!张建国!
这个名字像块冰坨子砸进心里。那个满脸横肉,走路像只螃蟹一样横晃的厂霸。
仗着后勤主任的身份和厂里那位副厂长姐夫,在厂区家属院横行霸道惯了,
占小便宜、调戏女工、克扣物资……大家敢怒不敢言。他居然打上了301的主意?
一股说不出的寒意顺着脊梁骨爬上来。昨晚那灯光,那歌声……难道……“哼!
”老孙头冷哼一声,“占死人房子?他也不怕折寿!
苏晚那丫头……死得不明不白的……我看这事儿,悬!”“嘘!”李婶赶紧打断他,
紧张地四下张望,“小声点!这话可不敢乱说!让张胖子听见,有你好果子吃!
”她端起刷好的盆,匆匆走了,脸色依旧难看。老孙头撇撇嘴,也端着牙缸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水池边,水龙头哗哗流着,冰水冲在手上,却感觉不到一丝凉意,
只有心底那股沉甸甸的、冰冷的恐惧在蔓延。张建国要搬进301?那个死过人的凶宅?
他真敢?!没过几天,消息就得到了证实。三单元楼下停了一辆厂里的破解放卡车,
几个穿着工装、神情麻木的工人正从车上往下搬东西:笨重的木头柜子,
蒙着厚厚灰尘的旧沙发,还有几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张建国本人就站在单元门口,
腆着肥硕的肚子,指手画脚。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紧绷绷的灰色涤卡干部服,
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几缕稀薄的发丝勉强盖住发亮的头顶。
他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得意和贪婪的笑容,小眼睛眯缝着,打量着搬下来的东西,
偶尔粗声粗气地呵斥工人动作快点。“轻点!轻点!妈的,弄坏了老子的红木椅子,
你们几个月的工资都赔不起!”他唾沫星子横飞。几个工人低着头,默不作声地加快动作,
没人敢反驳。筒子楼里不少人站在自家门口或窗户后面,沉默地看着这一幕,眼神复杂,
有好奇,有厌恶,有鄙夷,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忌惮和……难以言喻的恐惧。
那扇紧闭了半年多的301铁门,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工人拿着大铁钳,“咔嚓”一声,
绞断了门框上那条早已锈蚀不堪的铁链锁。门轴发出刺耳艰涩的“嘎吱——”声,
被缓缓推开。一股浓重的灰尘混合着陈年霉烂的气味瞬间涌了出来,弥漫在楼道里,
呛得门口的张建国都忍不住捂着鼻子后退了一步,连声咳嗽。那气味里,
似乎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难以形容的……像是东西捂久了腐烂的甜腥气。
阳光艰难地透过楼道尽头那扇蒙尘的小窗,照亮了门口一小片区域。
可以看到门内的水泥地上积着厚厚的灰尘,角落里堆着一些看不出原貌的垃圾杂物。
一股阴冷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门内是另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冰冷的世界。
张建国捂着鼻子,踌躇了一下,还是指挥着工人:“赶紧的!先把老子的床和柜子抬进去!
打扫干净点!多洒点消毒水,去去味儿!妈的,这鬼地方……”几个工人互相看了一眼,
眼神里都带着点犹豫和畏惧,但迫于张建国的淫威,还是硬着头皮,抬着沉重的旧家具,
小心翼翼地迈进了那扇洞开的、散发着不祥气息的门。我站在四楼楼梯口往下看,
正好能瞥见301门口的情形。看着张建国那副志得意满、仿佛占了大便宜的嘴脸,
再想到那晚门缝下的灯光和歌声,一股强烈的、冰冷的恶心感涌上喉咙。
他难道真的一点都不怕?他搬进去的那天晚上,筒子楼异常安静。
平日里晚饭后的喧嚣吵闹都消失了,各家各户似乎都早早关紧了门窗,
连小孩的哭闹声都很少听见。一种无形的、沉重的压抑感笼罩着整个三单元。夜深了。
窗外是浓得化不开的墨色。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毫无睡意。脑海里挥之不去的,
是门缝下的光,是沙哑的《夜来香》,是张建国那张油光满面的脸,
还有苏晚最后那个破碎的、躺在废墟里的身影。就在意识有些模糊,
快要被疲惫拖入睡眠边缘的时候——它来了。极其轻微,极其飘渺。像一缕游丝,从楼下,
从301的方向,透过楼板,丝丝缕缕地钻了上来。
“……夜来香……我为你思量……”不是收音机里那种沙哑的电流声。
这是一个真实的、年轻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空灵和……幽怨。
调子依旧是那支《夜来香》,但此刻听在耳中,却带着一种渗入骨髓的寒意,
每一个音符都像冰冷的针,扎在皮肤上。那声音,仿佛就在张建国那间新卧室里!
就在我头顶正下方的位置!我猛地睁开眼睛,心脏瞬间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
几乎停止了跳动。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向了四肢,又在下一秒冻结。耳朵里嗡嗡作响,
全身的肌肉都僵硬了。我屏住呼吸,侧耳倾听。四周死寂一片,只有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
但那歌声,消失了。死一样的寂静持续了几分钟,久到我几乎要以为刚才那一声是幻觉。
的神经稍稍松懈一丝的时候——“夜来香……夜来香……”那空灵、幽怨的女声又响了起来!
这一次,似乎更清晰了些,仿佛唱歌的人正慵懒地靠在床头,对着黑暗轻声哼唱。
歌声断断续续,却无比执着地在死寂的夜里回荡。是苏晚!绝对是苏晚的声音!
那种独特的、带着一点南方口音的柔软腔调,我不会听错!她真的……回来了!就在301!
就在张建国的卧室里!无边的恐惧像冰冷的潮水,瞬间将我彻底淹没。我猛地用被子蒙住头,
身体蜷缩成一团,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被子里的空气浑浊而闷热,
却丝毫无法驱散那股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苏晚的声音……她为什么回来?
为什么在张建国的房间里唱歌?那个雨夜门缝下的灯光……难道张建国搬进来之前,
301就已经“住”进了别的东西?一连串恐怖的联想几乎要撑破我的脑袋。被子外面,
那幽怨的歌声若有若无,像一条冰冷的毒蛇,缠绕着我的听觉神经,
每一次轻微的哼唱都让我抖得更厉害。冷汗浸透了背心,黏腻冰冷地贴在皮肤上。
我死死咬住被角,不敢发出一丝声音,生怕惊动了楼下那不知名的存在。
时间在极度的恐惧中被无限拉长。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难熬。那歌声时断时续,
像幽灵的叹息,固执地穿透楼板,钻进我的耳朵。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几分钟,
也许是几小时,歌声才渐渐微弱下去,最终归于沉寂。后半夜,我再也没能合眼。黑暗中,
我睁大眼睛,死死盯着低矮的天花板,仿佛要穿透那层薄薄的水泥楼板,
看清下面301房间里正在上演的恐怖景象。
每一次楼下传来极其轻微的、仿佛家具挪动的声音,或者只是老旧水管发出的“咯噔”声,
都让我惊得浑身一颤。张建国……他知道吗?他此刻睡在那张搬进去的旧床上,
是否也听到了这索命的歌声?天亮后,筒子楼恢复了表面的忙碌。但我注意到,
三单元的气氛明显更压抑了。邻居们碰面时眼神闪烁,匆匆点头便错身而过,
连客套话都省了。关于301,关于昨晚可能存在的“动静”,没人敢公开议论一个字。
恐惧像一层无形的冰霜,冻结了所有的声音。我也刻意避开了所有可能遇到张建国的机会。
一想到他可能就住在那个每晚传出苏晚歌声的房间里,
一种混杂着厌恶和更深恐惧的情绪就攫住了我。然而,有些事情避无可避。那天下午,
我去厂里锅炉房打热水。刚提着两个灌满热水的暖水瓶出来,就看到张建国腆着肚子,
正站在锅炉房门口和一个管事的说话,唾沫星子乱飞。他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同。
虽然依旧穿着那件紧绷绷的干部服,
依旧梳着油光水滑的头发现在看起来那几缕头发似乎梳理得更加一丝不苟,
努力地想要盖住更多的头皮,但那张油光满面的胖脸上,
却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疲惫和……烦躁。他的眼袋浮肿发青,像被人揍了两拳,
眼白里布满红血丝。往常那种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神气劲儿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神经质的、容易受惊的敏感。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眼神却时不时地飞快瞟向四周,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惶。
当锅炉突然发出“嗤”的一声排气巨响时,他整个人都明显地哆嗦了一下,差点跳起来。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废物!都是废物!”他对着管事吼着,
像是在发泄某种无处安放的情绪,声音嘶哑,透着股外强中干的虚张声势。
管事唯唯诺诺地点头哈腰。张建国烦躁地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转身就往回走。
经过我身边时,
一股浓重的、劣质花露水混合着汗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药味像是安眠药?扑面而来。
他根本没看我,或者说,他根本没心思看任何人,只是皱着眉,
嘴里似乎还在无声地嘟囔着什么,脚步匆匆,像急于逃离什么可怕的东西。
看着他远去的、显得有些仓惶的背影,我提着暖水瓶的手心全是冷汗。他这副样子,
绝不是装出来的。恐惧,真实的恐惧,已经像跗骨之蛆,缠上了他。那每晚萦绕不去的歌声,
他一定也听到了!301房间里,到底在发生什么?恐惧和一种病态的好奇心像两条毒蛇,
在我心底疯狂地撕咬、纠缠。理智告诉我应该远离,远离那扇门,远离那个房间,
远离张建国和他带来的所有不祥。但另一个声音却在疯狂地怂恿:去看看!靠近点!
也许……能发现什么?发现苏晚回来的真相?这种矛盾的拉扯几乎让我分裂。白天,
我强迫自己像往常一样工作、吃饭,努力表现得正常。但每当夜幕降临,筒子楼被黑暗吞没,
那熟悉的、幽怨的歌声从楼下301的方位准时响起时,所有的伪装都瞬间崩塌。
“……夜来香……吐露着芬芳……”空灵的、带着南方口音的女声,穿透楼板,
清晰地钻进我的耳朵。它不再断断续续,而是变得连贯起来,
甚至……带上了一丝难以言喻的“亲昵”?仿佛唱歌的人正依偎在熟睡的人身边,
对着他的耳朵低语。每一次歌声响起,我都感觉自己快要疯了。我用枕头死死捂住耳朵,
但那声音却像能穿透一切阻碍,直接钻进我的脑海深处。冷汗浸湿了床单,
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楼下,张建国的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他听不到吗?
还是……他已经被这歌声折磨得麻木了?或者,他其实醒着,在黑暗中,
与那歌声的源头默默相对?这种日复一日的、缓慢而残酷的折磨,
让我的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白天,我的眼神也开始变得和张建国一样,
带着惊疑不定的闪烁。我开始下意识地避开人群,害怕被人看出眼底深藏的恐惧。
对301的探究欲,像野草一样在恐惧的土壤里疯长。终于,
在一个沉闷得令人喘不过气的午后,我找到了机会。张建国大概是去厂里开会了,
三单元楼道里空无一人。阳光从楼道的破窗户斜射进来,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我的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站在301门口,
那股熟悉的、混合着灰尘、霉味和消毒水的刺鼻气味更浓了。门紧闭着,
新换的锁在阳光下闪着冰冷的金属光泽。我犹豫着,指尖颤抖地拂过粗糙冰冷的门板,
仿佛能感受到门后那彻骨的阴冷。视线不由自主地往下移。门缝。
那道狭窄的、不足一指宽的门缝。鬼使神差地,我弯下腰,屏住呼吸,眼睛凑近了那道缝隙。
网友评论
资讯推荐
最新评论